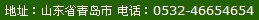|
——走近老河口丝弦文化 撰文/摄影江南久久/简白 上世纪之初,位于鄂西北、汉水中游的光化县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众多商贾云集于此,形成繁荣经济之势,更多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带着各地各方的艺术来此荟萃。于是,这里的曲艺、民乐更趋繁荣。据传在野园北面建起的中华楼,一楼唱戏,二楼说书,场面很是热闹;牛绳道子的打绳场成为曲艺、杂耍露演的场地,捧场观众来自各行各业;各会馆、茶社、戏园甚至庭院、货栈,那也是夜晚开唱迎客,白天练功吊嗓。那时老光化的街头巷尾,尽数吹拉弹唱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长久以来,民间文化在这里得到积淀、传承,其丰厚的底蕴润泽着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养成了纯良古朴,优雅闲适的民风!老河口丝弦文化就是在这种人文背景里,得到了良好的延续与升华!时至今日,更有一群人,坚持以各种方式,为继承、发扬和保护这份民间瑰宝而不懈努力!早在七年前曾作过相关报道的襄阳晚报记者刘文生,为我这样描述:“故事相当精彩,人物分外优雅”! 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河口传统音乐“老河口丝弦”榜上有名。年8月,文化部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公示,老河口民间传统打击乐“老河口锣鼓架子”名列其中。这两个“非遗”项目的申请成功,是对一位七旬老人毕生奉献老河口丝弦文化的最好安慰!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老河口市群艺馆退休干部,老河口丝弦传承人,老河口两项“非遗”项目的整理与申报者余家冰老师。 初见余老师,我脑海里立马浮现的词汇就是“知性优雅,与众不同”。当时,她从门外走进屋子,娇小(请毋庸置疑我的措辞)的身体沐浴在阳光里,白皙的面容带着浅笑,那份超凡脱俗的气质,迎面而来。 余老师利索地整理着她一头花白的短发,与我携手落座后,针对我们的来访,思路清晰、言词精妙地为我们讲述着她心目中的老河口丝弦文化。她说“老河口丝弦是文人学士、自由职业者自娱自乐的、市民市井的庭院式音乐,也就是室内音乐,不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五句子,三句子的乡间音乐。这种音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极高雅的艺术气息。老河口丝弦是从大调曲子(也就是板头曲)的前奏里分离出来,用古筝、三弦、琵琶等乐器演奏的弹拨类音乐,咱们老河口丝弦弹唱,是曲艺大调曲子的说唱类艺术。从真正的学术角度定义,是老河口这块土地上共生共长的两个艺术门类。老河口丝弦是国家级“非遗”,丝弦弹唱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由河南南阳率先申报,这是必须清楚的两个概念。” (解放初期老河口丝弦演出剧照) 以前的老河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水旱码头,南来北往的人们带来各地的优秀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生根开花。据传,老河口丝弦源自于乾隆年间的汴梁小曲,是由河南民间艺人带来的丝弦音乐。后来,通过格调高雅的文人学士、自由职业者按照自己的性情,结合本地音乐风情,语言习惯,不断演绎,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具有老河口特色的丝弦音乐。这种洋溢着阳春白雪风格的音乐在民间广泛流传,经久不衰。 时间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虽处战乱时期,因为那座铁打的古城襄阳作为战争前沿,屏障一般地庇护着当时的光化县城,让这个安全的小后方成了繁华的“小汉口”。城里活跃着一二十个丝弦班子,每到晚间及节假日,在茶馆以及商行的庭院内,总是一派悠扬婉转的丝弦之声。时事虽然动荡,但人们在浮生中偷得逍遥,以音乐中寻得抚慰,日子也就优哉游哉地打发走了。 但是老河口丝弦的现状却令人堪忧,自从那些老艺人们相继去世,擅长者已是寥寥无几。余老师说,这些能带给人心灵慰藉的传统文化艺术,必须依靠人来继承和发扬。否则,就如师傅所言:“人在艺在,人亡艺亡”,那样的结局将是不可逆转的损失,是对祖先最大的背叛! (已故王直夫老人演出剧照) (老艺人王直夫在辅导余家冰弹奏古筝)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余家冰与她的师傅、当年老河口丝弦“魁首”王直夫先生结缘于光化县杨家巷南头。中医世家出生的王直夫,自幼酷爱音乐,禀赋聪颖,后师从河南盲眼老艺人李瞎娃儿。因其擅长古筝、三弦、琵琶、洞萧、二胡、唢呐、锣鼓等民族器乐演奏,精通各路音乐,熟悉南北小调,对河南大调曲子和板头曲更有创造性研究,艺术造诣极深,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被公认为老河口音乐界魁首。而出生音乐世家的余家冰也是天资聪颖,看乐谱过目不忘,听旋律过耳不乱。音乐带给这一对师徒的机缘巧合,注定了老河口丝弦文化必将再次书写传奇! (老艺人王直夫在辅导余家冰弹奏古筝) 9岁那年,小姑娘余家冰执一横笛,为杨家巷口独自弦乐的王直夫先生悄然伴奏,让老人欣然认作爱徒。一条小巷,一方木桌,一架古筝,一位老者,一个小丫,开始了与丝弦相伴一生的师徒情缘。从此,余家冰与老河口丝弦血脉相依,无论是民间艺术被批斗为“封、资、修”的动乱时期,亦或是当下物欲横流的享乐年代,她始终潜心执着于老河口丝弦的学习、整理、深入研究、严格规范,几乎从未停歇过。 为了更好地发扬光大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她不仅勤奋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文学素养,便于更深刻地领悟众多曲牌里表达的思想情感与内涵,还认真搜集整理老河口地区内的各类民间文化,在此基础上,将老河口丝弦进一步提高,使音乐的地域特色更加鲜明,内涵更加丰富。余老师说“本地区的民俗文化、民间音乐,我虽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采集到,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我都去用心了解,认真记录,系统整理。这些民间艺术是一份失去便不可再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以抢救的速度去保护! 余老师拿出她从年开始有意识整理,后多次修订,手工抄录装订成册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老河口分卷》,这本书约50多万字,记载了老河口丝弦的全部曲牌演奏方法、历史渊源、传承情况、艺术特征等。她随手翻开一页,为我们讲述了众多曲目中的一首,名为《打雁》。她说,大雁的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大雁夫妻是真正从一而终的夫妻,如若其中一方不幸早逝,另外一方必将终生不嫁不娶,而家庭中的任何一名成员如果遭遇不幸,整个家族一定会守在那片遇难的天空,不断地盘旋、呼唤、哀鸣,久久不肯离去,这些不抛弃不放弃的动人故事与场景,我们老河口丝弦都可以很好地用音乐用旋律表达、演绎出来,那种来自于汉江水赋予的灵感,让我们能更秀气更细腻更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些情愫。说到这里,激情充沛的余老师双手相握,摸着自己的心口,然后又向我们张开,“你们说,这么美的音乐给了我多少幸福,让我怎能不好好享受,不尽心尽力地保护并传承下去呢……” 在这里,我愿意连篇累牍地叙述着我眼里这位丝弦艺术家。我无法想象在她瘦弱的身体里到底蓄积着多少热爱,可以让她几乎穷其一生,全身心投入到她挚爱的民间音乐里。她浑身焕发的那种热情让我始终无法将她与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联系在一起。浸润着老河口民间音乐的精髓,汲取着汉江水的清澈灵动,承接着鄂西北的浑厚地气,余老师的容颜是年轻的,她的谈吐是年轻的,她的气质更是年轻的! 秀美优雅的余老师讲述这些时,我们正在她的家里,听完她与她的搭档为我们弹拨演唱的一首《渔樵耕读》。她端坐在那架古色古香、大气沉稳的“竹吟风”古筝前,举手轻拨,清音旋起,“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即使是弦乐门外汉,也瞬间醉进了那精妙绝伦的旋律中。余老师与她的伙伴们,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物我两忘的神情,更是让我们深深地体会了老河口丝弦的无穷魅力! 就在我们为这美妙的音乐陶醉时,一位临窗而坐,面呈病容的偏瘫老人,一直温情地笑看着这一切。这是余家冰老师的爱人蔡老先生。原来早在十九年前,54岁的蔡先生就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溢血重患中,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这么多年,余老师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除了整理丝弦曲牌,教授年轻学员,就是照顾病中的爱人。她说在老伴生病之前,她作为家庭主妇,从来不关心家里的柴米油盐,爱人总是在工作之余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好好的,全力支持她的工作。因为那些年安心学习、整理积累的资料,才有今天进一步科学系统地分门别类。所以,余老师感激爱人,再忙再累,也不怠慢这份尽心的照顾。想起上楼时,余老师握着我的手说“他现在即使病中,思绪依然清晰,言语仍旧风趣,蛮好玩儿的一个老头儿。”回头再看着蔡先生安静地坐在那里,认真倾听爱人弹奏弦乐,想起诗经里的那句“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岂不正是这对爱人的现实写照! 当夜色盈窗,我们辞别出来,余老师坚持送我们下楼,并再次叮嘱我为老河口丝弦落笔为文时,一定要准确严谨。希望我们有时间再来,那时她一定带我们去看她的“青少年丝弦传承基地”。 按照宋玉玲老师电话里所说的地址,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老河口市的大巷子。在巷口向一位老者问路时,他得知我们寻访的是老河口丝弦弹唱中心,便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欣然要求给我们带路,并告诉我们要找的这群人在这里可受欢迎了,问他是否喜欢,他笑呵呵地说那是必须的! 见到宋玉玲老师的时候,她正在丝弦弹唱中心那间简陋的老房子里,带领十几位老人吹拉弹唱排练着。 一阵简单寒暄之后,乐器声响起,一位衣着打扮时尚的女士大方地走到房子中间,面向观众,一首《西厢记》婉转开唱了。为歌者伴奏的是六位先生,其中头戴深蓝色小檐礼帽的老者,未开场时,静坐一旁,默默不语,当他举起鼓棰,立马动若脱兔,神采奕奕,敲锣击鼓,有板有眼,煞是潇洒。特别精彩的是,当他举棰伊始,那些伴奏者的眼睛都一瞬不瞬地看着他手中的小木棰,只见棰落鼓响,那些弦胡笙箫的演奏同时发声,一时间含宫咀征何悠悠,抚掌击节乐陶陶……当他的鼓声最终一棰定音时,所有的演奏说唱也同时收声,有那么一瞬,因为这种突然的安静恍若时光也于此驻足,仿佛在这一刻被穿越了古今,那份如梦方醒、心满意足的感受随之漫上心头,畅快! 虽然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地方性民乐,一曲歌罢,那一声“好”字的喝彩,正是发自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原来,音乐是不设限的,本民族的音乐更是如血液般,一直就流淌在自己的身体里,那边民乐声响起,这边热血已沸腾! 宋老师说,老河口丝弦弹唱虽然源自河南曲艺的大调曲子,但自从年前流传至襄阳老河口之后,在这座汉水之滨的繁华之地,已逐渐演变成民间艺人行艺和文人学士自娱的音乐,能够爱上这门艺术的人们,内心都是高雅脱俗,追求完美的。 说起老河口丝弦弹唱的历史,老人有那么一阵子陷入沉思。之后宋老师谈起了她与父亲结缘这门曲艺的各种往事。 原来,她祖籍河南邓县,父亲八岁那年,身为私塾先生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年幼的父亲被迫流落江湖。多年以后返回邓州时,父亲已是一位能弹会唱大小曲子的生意人。待到小玉玲记事时,家中杂货店里总是高朋满座,吹笛子的,拉二胡的,敲锣鼓的,这拨刚走,那拨又来,管吃管住管开心。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小玉玲,耳濡目染各种曲目的曲调和歌词,小嘴一张,说唱即来。十岁时,被邓县曲艺团看中,便跟着那些南阳来的老师们,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弹唱艺术生涯,所以宋老师现在的演出,也是带有浓郁南阳地方特色的老河口丝弦说唱。 宋老师与老河口丝弦弹唱的缘分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夏天,当时她来舅舅家做客,无意间听说光化县城新成立了一个曲艺队,正在招演员,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应试,结果被老师一眼看中,怎么也不放她走了。于是,她成了光化曲艺队的一名队员,随后,与同样年轻的丝弦演奏员余家冰成了搭档。从此,这一弹一唱的组合随着时代变迁,世事沉浮,再也没有分离过。及至今日,余家冰与宋玉玲这对黄金搭档的默契程度,已经不用言谈举止交流。技艺炉火纯青的两位老人,在表演过程中,只是一声气息,一个眼神,便可知对方接下来的曲调、唱词将要合在哪一个重音上…… 采访中,我们有幸目睹并倾听了余老师与宋老师合作的一曲《渔樵耕读》,那幅“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的画面让人感叹不已。余老师的古筝之音清越绕梁,久久萦绕耳畔,撩拨心弦,宋老师字正腔圆,大气沉稳的说唱也是字字句句,落在心坎。只见她左手轻举平肩,右手执一檀板,跟着古筝三弦的音乐打着节拍,接着亮起嗓子,古头说唱开场了: 渔翁垂钓,樵夫登高, 农夫耕田望田苗, 读书人,十年寒窗把名标…… 李太白酒醉后水中把月捞, 商纣王贪色把江山丢了, 石崇今何在,小周郎命早消, 看起来,酒,色,财,气无有下梢…… 酒色财气,人人爱好, 冒犯法津命不牢, 奉劝大家,听我忠告, 唯有那,琴,棋,书,画是情操! …… 无论艺术的滋养,无论岁月的馈赠,在宋玉玲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感恩。她从心底里热爱着老河口丝弦文化,并立志要将这种爱传递出去,带给老河口这座城市的广大市民。她说“我们这个中心的活动场所,是中心成员自发出资租用的,大家非常齐心,其实就是缘自于丝弦弹唱这一共同爱好!我们热爱这门民间艺术,每天排练这些曲目,归根结底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要还给养育了这些音乐的这一方水土和这里的人民,所以我们要走出排练厅,走到群众中去,让观众在享受中与我们一起热爱,一起传承,只有这样,这些宝贵的东西才能从我们的手中一代一代传下去!” 为了节目创新,符合时代主题,谙熟丝弦弹唱韵律、格调的宋老师就自己动手,编撰歌词,段子,故事。比如说很受城乡人民欢迎的《老河口的身边事》;还有那个宣传孝顺老人的新故事《好媳妇》,只要表演,准能感动台上台下一大片。因为这些用心的创作与演出,赢得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每周日在公园的公开演出活动中,有许多观众就是冲着他们的节目去的! 弹唱如风自然来,艺苑生花传馨香。热爱老河口丝弦艺术的人们还在往这里聚拢,无论老人还是小孩。宋老师说她无怨无悔地做着这些工作,就因为这是爱了一辈子的艺术,是的确能给人们身心带来愉悦的传统音乐,她希望通过她的努力,在她有生之年,用最实际的行动,帮助更多的人们来北京白癜风治疗最好的医院在哪北京治疗白癜风到底需要多少钱
|
当前位置: 老河口市 >汉江有花开清风自然来走近老河口丝
时间:2017/10/2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老河口要大发展了被国家列为新型城镇化试
- 下一篇文章: 老河口市2016年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