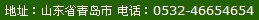|
为垦荒精神立丰碑,为红色题材树典范 ――评台州乱弹《我的大陈岛》 文/李小菊近些年来,编剧陈涌泉的创作有几个明显的变化特点,首先,以《程婴救孤》《风雨故园》《阿Q与孔乙己》等作品为当代河南戏曲做出巨大贡献的他,开始把创作精力和合作眼光投射到全国,先后为湖北、浙江、河北等地创作了多部作品;其次,以历史剧和文人剧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赢得艺术声誉的陈涌泉,在当前大力提倡现代戏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了一批现实题材、红色题材的戏曲作品,这些作品无不斗志昂扬,激情澎湃,形成了具有陈涌泉自己艺术特色的现代戏风格;第三,陈涌泉创作的这些现代戏,都是为地方基层戏曲院团的小剧种或稀有剧种创作的。就笔者近年来所观看到的陈涌泉创作的这一批作品,有湖北省老河口豫剧团的豫剧《黄河绝唱》、河南省三门峡市青年蒲剧团的蒲剧《布衣英雄》以及浙江省台州市乱弹剧团的台州乱弹《我的大陈岛》等。在这些作品里,台州乱弹《我的大陈岛》是最能代表陈涌泉当前创作特点的:红色题材、地方剧团、稀有剧种,因为无论是湖北的豫剧还是河南的蒲剧,从剧种本身来说都是有着省际影响的大剧种,也都与河南籍的陈涌泉有着直接关联,而浙江台州的稀有剧种乱弹,对于河南剧作家陈涌泉、对于全国观众来说,都是陌生化的。就是这样一个对于陈涌泉来说有着陌生化含义的剧团、剧种、剧目,陈涌泉却给它取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代入感和浓烈情感投入的剧名:“我的”大陈岛。这不能不引起观众的好奇心:这个大陈岛是谁的大陈岛?是陈涌泉的?是剧中人的?还是台州人的?《我的大陈岛》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重建浙江台州湾东南海域大陈岛的事迹。年国民党军队败退撤离大陈岛时,带走了岛上的全部居民,炸毁了一切军用和民用建设,埋下了数以万计的地雷,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荒岛、死岛。为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号召,年到年间,先后有名年轻人到大陈岛垦荒,把大陈岛重新建成了充满勃勃生机的绿洲。陈涌泉在《我的大陈岛》创作谈中这样写他到大陈岛实地采风时的感受:“那天细雨蒙蒙,满眼苍翠都笼上了一层薄薄的细纱,几分朦胧,恰似历史烟云。望沧海,我仿佛看到了一群花季年龄的垦荒队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等过春节便乘船向大陈岛驶来,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激情和渴望;看山野,我仿佛看到这些刚登上大陈岛的年轻建设者们正挥汗如雨……”陈涌泉用一个最有自我意识的标题,创作出一部最具忘我精神的作品。他把对题材、对人物、对时代的热情与激情,全都投注到作品之中,去表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去塑造那些忘我奉献的青年,去歌颂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之所以会这样,大概是因为陈涌泉总是能准确地把握住每一个题材的主旨、每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每一个人物的灵魂,无论是程婴的忠义还是朱安的隐忍,无论是《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的革命主义创作激情还是布衣英雄陈廷贤的光辉与痛苦,都是如此。正是这种创作的激情和对创作对象强有力的把控能力,使得陈涌泉在驾驭“大陈岛”这个“命题作文”的时候,采取了“正面强攻”的写作方法,直面时代与使命,直面激情与青春,直面奉献与牺牲,这样的选择,既是剧作家的能力与担当,也体现出男儿血性。 从总体上看,该剧宏大场面铺排与局部精细描刻并重,垦荒人的群像塑造与个体刻画相得益彰,战天斗地的革命激情与浓情蜜意的儿女柔情交融。而实现这种宏大与微观、群体与个体、激情与柔情顺利转换与连接的,是自然的视角转换和连贯的情感传递,这使得全剧脉络清晰,气韵流畅,给人酣畅淋漓的观剧感受。驻守大陈岛的解放军官兵敲锣打鼓地期盼垦荒队伍的到来,但他们敲的“锣”打的“鼓”是脸盆和炮弹壳,这样的开场,瞬间就把大陈岛上人的激情与物的贫瘠表现出来。垦荒队员登岛了,他们是一批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大陈岛”的热血青年,他们的到来给荒芜的大陈岛带来忙乱和生机,他们中有晕船却不让战士背的性格坚强的李招娣、怀揣音乐梦的金怡人和他娇气的恋人王逸琼、拥有篮球梦要建体育场的栗观成,以及为婚事而操心的大龄单身男青年张丰春……就这样,一个个出身经历不同、脾气禀性各异的队员形象鲜活地出现在舞台上,他们每个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极富个性,而且他们对后面的剧情发展都将起来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忙乱之际,驻军团长单智勇向团市委特派专员王大山询问怎么不见名单上的女团支书,王大山回答“她叫叶青青,一登岛就近不及待地勘查‘垦荒战场’去了”,不但巧妙地引出了女主人公,还侧面塑造了她的形象,让观众对这个富有强烈事业心的姑娘有了初步印象。紧接着,伴随着叶青青的幕后演唱,场景一转,大陈岛的另一面,身背行李的叶青青站在高处俯视着满目疮痍的大陈岛,心情既痛惜又激愤,忍不住发出“何时才能驱死寂,重让荒岛现生机?”的诘问,并暗暗下了“我一定要让大陈岛早日重现生机”的决心。就这样,充满动作张力的叙事性语言与景随事转的舞台设计完美衔接,作品叙事的重心从垦荒队登岛的全景表现转到了主人公叶青青的身上,就像是影视剧作品里的全景镜头摇移推拉,叶青青就这样出现在观众面前。叶青青不但是个有性格的人,也是一个有前史、有故事的人,她一出场,身边就如影随形地出现了一个追随者陈金良,垦荒人的浪漫爱情史也由此自然而然地展开了。他们已经订婚,但是面对建设大陈岛的重任和众多的垦荒队员,身为团委书记的叶青青对待陈金良显得矜持而克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垦荒事业未竟,二是因为她觉得陈金良还有待考验,这样的恋人关系和恋爱心理,非常符合女孩子的恋爱心态,使得二人的相处关系显得富有情趣。他们这种相互依恋又相互考验的情感,通过叶青青一句“能不能结婚,看你在大陈岛的表现”,将二人的情感融入建设大陈岛的事业之中,又通过凤尾山顶宣誓,通过一个个宣誓人自报名字,把作为个体的叶青青和陈金良,融入到垦荒队这个集体之中,就像摄像机镜头,从特写换成了全景。以上分析的是《我的大陈岛》第一场的叙事特点,这一特点在后面的场景中多次出现,如第二场劳动工地一场,首先是凤尾山上不同劳动场景众人劳动的群像,幕后伴唱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扛起锄头,第一次挥起铁镐;第一次担起水桶,第一次拿起镰刀;第一次赶起牛群,第一次放起羊羔……”然后是每一个垦荒队员讲述自己的劳动感受:金怡仁(唱)第一次肩头像火烧, 金晓云(唱)第一次双手打血泡。 栗观成(唱)第一次两腿似灌铅, 戴香娥(唱)第一次仿佛累断腰。 金怡仁(唱)第一次离家这么久, 陈岚芬(唱)第一次想娘泪暗抛。 栗观成(唱)第一次在外过春节, 金晓云(唱)第一次亲人隔海遥。 王逸琼忍受不了这种劳动强度堵气走了,她最终还是没有坚持到底做了逃兵。这时叶青青和陈金良挑着担子相继出场,陈金良依然跟在叶青青后面,叶青青为实现建设大陈岛的目标时刻以苦为乐,陈金良为通过心爱的姑娘的考验忍受着苦与累。陈金良也用自己的方式考验着叶青青,他假装踩到了地雷来考验心爱的姑娘心中有没有自己,结果却弄巧成拙惹得叶青青拂袖而去。陈金良一语成谶,他终于通过了叶青青的考验,却没有等到她穿上大红的布拉吉与自己结为连理,他为救队友踩中地雷光荣牺牲了……既表现创业的激情,又直面奉献与牺牲,既表现浪漫与豪情,又表现悲情与壮美,这是《我的大陈岛》带给我们的多样情感经历和审美体验。作品对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表现还通过齐心合力战台风、画饼充饥过除夕等场景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而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则又是通过细部的、个体化的单独叙述来表现,这就是养猪人张丰春的妻子王莲女产子一场。面对张医院生产的决定,王莲女不愿离开丈夫,也不愿离开即将生产的母猪,家里的棉被被母猪拖去垫窝了,吃苦耐劳的王莲女就这样在艰难的条件下与委屈的心情中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大陈岛上的“垦二代”就这样诞生了。《我的大陈岛》充分表现了陈涌泉红色题材戏曲创作的特点,他敢于直面题材的挑战,善于表现宏大场面,能够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并通过饱满的创作激情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丰富情感,因此他的这类作品总是激昂慷慨、振奋人心。红色题材戏曲创作,决定了这类作品必然要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创作的方向和宗旨,《我的大陈岛》做到了,陈涌泉做到了。该剧的舞美设计也延续了剧本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完全服务于叙事需求,成为完成情节推进与人物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决定了该剧的舞台设计风格也是现实主义的。我们批判舞美大制作,是因为这些作品往往为舞美而舞美,昂贵而笨重的巨大道具僵硬又呆板地摆在舞台上。《我的大陈岛》的舞美,就是一座巨大而高耸入云的大陈岛位于舞台正中央,把孤悬海外的大陈岛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岛屿周围的舞台空间,既可以是奔涌在大陈岛周围的浩渺大海,也可以是演员表演的舞台空间,而这座“岛屿”是可以转动的,因此它的前后左右、上下里外,都是不同角度的大陈岛,是垦荒人的劳动与生活、激情与爱情发生的场域。因此,观众真实地看到了垦荒人弃船登岛的情景,众人四处寻找团委书记叶青青,转台一转,岛转景移,初登小岛四处查看的叶青青就出现在半山腰;等叶青青号召大家登顶宣誓时,转台再转,全体垦荒人员就出现在小岛的各个方位。而整个岛的内部是中空的,里面是垦荒队员们居住的房屋,当所有房屋里的灯光点亮的时候,特别温馨又充满生机。这个“岛”还给喂猪的张丰春专门辟出一角,他的妻子就在里面生产,外面就是他的猪圈。最后,“大陈岛”变成了一艘风帆高张的机帆船,既是牺牲了的陈金良的心血体现,也是前途远大的大陈岛驶向未来的象征。该剧的道具全方位展现大陈岛全貌及垦荒生活,真正使舞美道具做到了物尽其用,极其灵动,体现了具象与抽象并存的舞美设计运用理念。《我的大陈岛》对台州乱弹的剧种建设和剧团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方向性指导作用。据台州市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说,他们正在创作的下一部作品,名字就叫《我的乱弹我的团》,《我的大陈岛》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具有当代意识的优秀作家、作品,像一剂强心针,激活了弱势剧团、稀有剧种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该剧的唱腔和演员的表演来看,柔婉的江南剧种台州乱弹,在表现红色题材、宏大题材方面是完全胜任的;在音乐设计和乐队配器方面,尚有可探索的空间,该剧在这方面坚持了乱弹的传统乐队配置和创作原则,在烘托宏大场面和激烈情绪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也成为该剧艺术方面唯一的缺憾,在这一方面,无论是该剧还是台州乱弹今后的创作,其实完全可以借鉴已经在戏曲作品特别是现代题材戏曲作品中普遍运用交响乐队的新的音乐传统,以开放的创作心态和现代的创作理念,打通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音乐脉络,让所有的音乐样式、艺术样式以融通和谐的方式,为剧目所用,为剧种所用。原文发表于《戏剧文学》年第7期。图片来源于网络。文字、审核/四戒斋主 排版/五月 三人行游于艺 长按
|
当前位置: 老河口市 >李小菊为垦荒精神立丰碑,为红色题材树典范
时间:2021/9/3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发布大量4月12日最新的优质微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